打破壁壘——博物館面臨數字學習的機遇與挑戰(三)
“我将開拓一條新的道路,探索未知的能量,解開這個世界最深奧的創造之謎。”
——瑪麗•雪萊編劇《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
雖然新的學習技術振奮人心,然而衡量其影響的标準卻寥寥無幾,或者說,這種新技術之所以湧現是因為其它的學習方式落伍了。并且,遠程學習發展勢頭如此迅猛,是否會給創造它的機構帶來挑戰,并發展成一個無法控制的科學怪獸?
Wayne Clough将這些觀念一一分解。他說:“人們總是想看到真實的物體”,并以史密森博物學院美國國家曆史博物館收藏的最古老的星條旗舉例。人們觀看星條旗的電子圖片“與置身現場看到有些老化的旗幟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也無法感受到這件實物在我們曆史中的位置,在現場還可以和其他50人一起感受這種不可思議的自豪感和敬畏感。”
不過,作為一個博物館是否必須具備一般博物館的那些屬性?2011年啟動的谷歌藝術計劃是一個大型的在線數字藝術品平台,其中囊括了從世界各地558個博物館中精選的11361件藝術作品,大多數還附有詳細的說明和視頻。這是一個擁有衆多元數據的元博物館,但是,這是一種博物館體驗嗎?這些二進制位的電子化信息是否如DNA的活體堿基對一樣強大?Clough說:“大體量和包羅萬象并不會讓觀衆買賬。隻有變得優質,隻有滿足人們的需求,才會真正奏效。”
那麼,什麼才管用呢?在沃斯堡曆史與科學博物館的會議上,與會者對當前正在發展中的Oculus Rift虛拟現實眼鏡意見不一。這種眼鏡的價格将近350美元,看來似乎已經解決了分辨率的問題,性價比合理,延遲低,也就是說,當你轉頭的時候,影像不會明顯地模糊。它的功能類似于可戴在頭上的天文館,顯示着諸如從太空俯瞰地球之類的影像,地球的曲線和藍白地表仿佛觸手可及。低下頭,你可以看到國際空間站從你的腳下飄過。轉向左邊,地球緩緩遠去,你遁入太空,然後就看到了月球。
這樣的效果非常炫目——當然這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美國西北大學副教授、獲微軟研究院贊助的全球望遠鏡計劃的工程師Doug Robert說: “如果這種體驗如此強大,為什麼要去博物館?”
稍遜于虛拟現實眼鏡的是電子寫字闆設備,如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使用的“一号展廳”(Gallery One)。觀衆可以将寫字闆帶入博物館,将它放置在藝術作品前,屏幕上就會顯示像“誰是創作者”“它的主題是什麼”一類問題的答案。使用者還可以學習藝術作品的曆史背景知識。例如,對于一個在紐約展出的關于經濟大蕭條繪畫的展覽而言,這種設備可以解釋當時的社會狀況。
麻省理工博物館館長John Durant也參與了沃斯堡會議,他認為,“一号展廳”将參觀博物館的實際感官、數字探索與藝術性整合成為一個系統的參觀體驗。他說:“觀衆可以創造自己的體驗。你可以為自己策劃一個藝術展,并将其下載,作為博物館參觀的一個紀念物。”
數字學習方法效果如何?顯而易見的優點在于,它們可以轉變許多人對“博物館是什麼”的固有認知。科學技術中心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沃斯堡會議發言人Anthony (Bud) Rock說:“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研究所曾經對博物館觀衆體驗做過一次全面的調查。人們回想一下說,‘我們喜歡這個博物館’。”結果令人吃驚:在擁有美好的博物館體驗的人中,75%的人并沒有實地參觀過博物館。他說:“我确實被這個統計數據震驚到了。這告訴我們,實體博物館之外的拓展是多麼重要。”
另一方面,他說,數字學習可以構建真實的博物館體驗。一個例子就是波士頓科學博物館納米醫學探索網站的“給老鼠看病”展覽。用戶要利用幾個圖像和文本證據來診斷老鼠的癌症病情。Rock認為,雖然這隻是一個虛拟體驗,但是卻可以激勵人們的學習。他說:“大多數人都表示,‘看到你們的網站給老鼠看病,真的好酷。’數字學習驅使人們走近博物館,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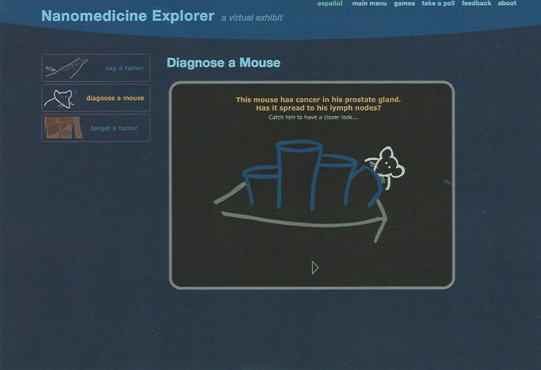
史密森博物學院已經為其“X3D”項目投入巨資,這個項目是為了增加藏品的展示維度,比如美國革命戰争幸存下來的戰艦“費城号”。如果你在美國國家曆史博物館中看到了這艘戰船,你的視線将會局限于它的首舷角。但是,利用3D拍攝技術,在線浏覽者可以看到這艘船最初的樣子,也可以看到它水下的結構。同樣地,博物館還利用3D打印機制作了亞伯拉罕•林肯的一系列仿真人像,對比他當上總統時和四年後的形象,可以清楚看到内戰中這位國家最高統治者所經受的壓力。
美國曆史博物館的Kotcho說:“所有的技術都令人振奮,我們要與最新的技術保持同步,時刻走在前列,但是,利用最好的技術的宗旨在于滿足觀衆的需求。”
史密森學院的Clough說,這些努力需要人來買單,但是,買單者不應該是那些博物館常客。他建議,博物館應當向私人捐贈者和基金會募集資金,像蓋茨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等,他們就曾為史密森博物學院的數字計劃提供資助(盡管我們并不清楚,有多少博物館可以擁有這種高層次資助的機會)。雖然史密森學院的核心資金來源于政府,但是,它的數字發展主要依靠其它資金的支持。Clough說:“博物館控制自身的發展方向至關重要。”
沒有發動機,飛翔有可能實現;但是,沒有知識和技能,人類永不可能翺翔天際。
——威爾伯•萊特
Clough在其著作《兩個世界的精華:數字時代的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中寫道,博物館在适應數字環境的過程中遭遇了艱難的時期,部分原因在于技術不足,以及博物館文化“過于重視策劃展覽以至于忽略了向公衆提供更為開放的資源”。不過,他說,結果顯而易見:“這些機構要麼接受數字技術,否則将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或許,“博物館”一詞最終可能會被定義為動詞,而非現在所理解的名詞。它将變成一個充滿了互動性的所在——從建築物自身(如果存在的話)到家庭辦公和學校教育。不管作為媒介還是方法,就像它的詞根所昭示的一樣,一個博物館應當化身缪斯(muse)。知識是驅動引擎的燃料。
早在1903年,博物館就為萊特兄弟的發明提供了支持。他們設計制作的“飛行者1号”(Flyer 1)擁有12匹馬力的引擎,他們的木頭雙翼飛機僅僅覆蓋着布面。但是,史密森博物學院為他們的設計提供了重要的數據。
公道地說,美國博物館數字技術時代已經啟航了。就像萊特兄弟一樣,我們還處于此次航行的起點。隻要遵守基本的規則,博物館可以毫無顧忌地前行、上升。創造智慧,用盡可能合理的方式傳播知識,與觀衆緊緊相連,屆時,您的博物館定能翺翔天際。
全文完。
(原作者Jeff Levine,劉平編譯,美國博協《博物館》雜志2015年7、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