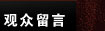向京:参展艺术长沙,将是作品与空间的较量

【导言】近几年来皆以高调著称的“艺术长沙”自2007年成功举办以来已经举办了三届,展出了包括长沙本土艺术家在内的20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赢得国际艺术界的瞩目。艺术长沙是由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发起,与湖南省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文化艺术品牌。据悉,2013年第四届“艺术长沙”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将于10月份在长沙市博物馆拉开帷幕,并将推出周春芽、郭伟、向京、丁乙四位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向京将作为华北地区艺术家代表参加艺术长沙,这次向京将会为长沙市博物馆这个特殊的场地带来怎样的作品?作为一位当代雕塑艺术家她对长沙的当代艺术和城市文化发展又有怎样的看法?雅昌艺术网带着系列问题专访了艺术家向京。
雅昌艺术网:向京老师您好,今年是您首次参加艺术长沙,不知您与艺术长沙的合作是怎样开始的?您对长沙有怎样的印象?
向京:艺术长沙当年最早一期启动的时候动静比较大,比较高调,而且历届艺术长沙开幕的方式坊间都有许多流传,我觉得很有趣。但此前每届都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都没有去成,直到老谭(谭国斌)过来找我。
我跟谭国斌认识就是因为艺术长沙,而且他找我的时候还没戒掉他的槟榔,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挺有趣的。说实在话我开始的时候真有点儿搞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看不太懂,我对所有我看不太懂的行为都有点儿迟疑,但总觉得谭国斌为人比较有趣,我对有趣的人也比较感兴趣,他的想法比较歪,但很有想法,只是他的想法我不太摸得到他的思路,觉得他挺有意思。
另外我觉得当代艺术这么多年来,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很多,尤其是会有突然间冷不丁的进入到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很多,但也都去的快。所以我觉得艺术长沙做了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下来之后,开始看的时候觉得不太着调,不太相信他,但是他坚持做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你会觉得真有点儿挺不同的,当代艺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民间资金的注入带来非常大的活力和非常大的可能性,我觉得确实是说这些民间资金也被当代艺术的一些不守规矩伤害得很厉害,也跟当代艺术机制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很多民间资本和基金投入到当代艺术中,我们都觉得应该值得去鼓励和保护,所以我觉得很希望参加这样一种活动和展览。
雅昌艺术网:艺术长沙并不像北京或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在长沙这样一个当代艺术不太发达的城市建立起这样的大型展览您怎么看?
向京: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一开始不太看得懂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老谭最值得钦佩的地方,长沙肯定不能说是一个文化沙漠,但至少它在当代艺术这个领域一直是严重失语的,虽然湖南出了不少文化人和艺术家,湖南籍艺术家也非常多,但是在湖南本地产生的文化生态还是相对比较缺乏的。
我觉得这是中国挺奇怪的现象,理论上讲不管是艺术家的生活形态还是艺术行业的生态链条都应该平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城市,甚至可以是一些小型城市,当然是可以以一些重要的城市为主、为中心,艺术家应该是比较容易倾向于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但在中国就是一个比较畸形的发展时期,就目前这样的形态只有说甚至说可能很多大城市已经是从经济上强大起来,但是在文化上仍然还是很式微的,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单调和贫乏的。
所以我这么理解艺术长沙,对于湖南、长沙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些文化形态来说,肯定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觉得不管是被人怎样去妖魔化或者怎样去歪曲,但是从正面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先驱,可能就是因为谭国斌做艺术长沙之后星星之火可能燃烧起来了,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通过时间去验证的一个事情。
雅昌艺术网:今年的艺术长沙的展览场地改到了长沙市博物馆,策展人也由博物馆的馆长陈建民担任,怎么看待今年艺术长沙的改变,怎么评价这个展览场馆?
向京:长沙市博物馆是一个文革时的老建筑,我特别喜欢,建筑本身的建筑语言强烈极了,首先是我理想中硬件非常好的博物馆的形态,有非常大的绿化、湖、树林,已经变成当地老百姓去健身、交际或娱乐的公众空间的场所;而且就建筑本身而言,一个非常巨幅的毛主席年轻时候的头像,据介绍,这个头像当时做的时候用很多灯管,一个一个拼接成毛主席头像,这个东西在当时看来肯定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但现在看简直是一个当代艺术品。
展览场地也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博物馆的大堂,一看就是那个年代下的会堂或是大礼堂,上面有一盏特别好看的灯,同时一定也会给布展产生非常大的难处,“很不幸”这个大堂分给我了。当时老谭跟我讲:“你把这个大堂拿下来吧”,我说:“我才不拿呢,这么大一个地怎么弄,没法布展”他说:“你就弄一些大雕塑搁在这儿”。我说:“搁什么雕塑都会被吃掉的”但他还是把那个区域分给我了,说实话我心里挺忐忑的,因为在我自己布展经验里这样的空间自身语言太强烈,又没有特别专业的灯光,我觉得几乎是不能布的,任何一个作品搁上去都一定会被吃掉,何况它还被作为开幕和人来往的通道,我之前也碰到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空间,这个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处理的空间。

向京《异境—不损兽》玻璃钢着色,195×210×62cm,2011
雅昌艺术网:那打算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语言的空间?
向京: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永远是艺术家要面对的一个考试,空间怎样处理?尤其是做立体作品的艺术家常常要面对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空间不会给一个画家,画家不需要面对这样,他只要有一面白墙就行,展览就是你对画的理解,仅限于在一个白墙上平面的概念。
但是做立体作品的艺术家必须要和空间产生关系,尤其像我极其热衷做所有的情景设计,空间是我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像一个较量,一方面空间有它自己特别强的语言,一方面我自己作品又有很强烈的语言,就像两种力量,同时也是两种限制,你怎样处理这两种限制,这两种可能完全是不协调的两个东西,只能说非常冲突。即便是没有那么冲突,只要是不同都很难放到一起去,所以我到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大概会有一个区域划分。
雅昌艺术网:那参展作品会选择哪几个系列的作品?
向京:参展的作品数量并不多,算下来应该有七件作品,其中一件是一群人围着一圈洗脚的那件作品,谭国斌点名要这件作品参展,但他的出发点非常可乐,好像是说长沙是“洗脚之都”的意思,跟长沙有些许关系。还有两件作品是为了刚刚谈到的博物院大堂考虑,相对比较完整的作品;其他几件作品的选择都是动物或者是跟动物相关的作品,构成一个跟动物有关的相对比较整体的一个面貌。
雅昌艺术网:您刚刚谈到谭国斌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想跟长沙文化产生关系,您也谈到您这是首次去长沙,能否谈一下您对长沙这个城市的文化有何印象?
向京:我对长沙这个城市非常不了解,以前去过几次,多半都是路过而已,也肯定了解不深,上次去长沙的时候我稍微转了转这个城市,我对长沙人的兴趣比对这个地方的兴趣要更大一点,因为湖南人就很有意思,都很聪明,但是很邪门,至少我这么看。“邪门”这个词并不是个坏词,是有意思的好词,理论讲湖南这个地方应该是特别诞生艺术家形态的人。
我这次去等于最近一次去艺术长沙以后,我觉得有一点让我特别不舒服,这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很多城市,那就是同质化严重。中国每一个城市变化都太大了,都是由一个很小的,很有特色的城市变成努力向所谓的大都市的心态去野蛮生长,在这种野蛮生长的速度和幅度里,死掉的东西太多了,无论如何在哪儿我看着都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长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特色、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当然里边保留了很多街道。
但是这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些老街保留下来可能是因为有利可图,要转换成商业价值,这也是我们现在文化非常可怜、可悲的地方,我觉得当代艺术肯定会有非常多艺术家的作品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希望这样的问题能够引起特别广泛的重视,这就意味着特色的文化永远是一个在消亡的文化,并不是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就有怎样的壁垒,恰恰是你失去了你自己的特色,你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循环,在我理解全球化理想概念是多元化的,意味着不同、共存,并不意味着一体化,意味着大家都是一样的面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当中特别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雅昌艺术网:在长沙这样的城市他本身可以说是当代艺术并不是特别发达,您作为一个当代雕塑艺术家,怎么看待这个城市的当代艺术和城市雕塑的发展?
向京: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是跟艺术生态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第二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很难在短期能够实现的东西?我觉得这跟体制还是有关系,跟艺术生态不健全,导致普通大众和艺术的距离远极了,比如说所谓的公共教育环境问题,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你能数得出来有几个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会想到去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当代艺术的发展现在这么引人注目,多半是因为市场的引导,是因为有一些价码在前边标着,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投资、可炒作的东西一样,媒体对它的关注,普通人多少知道一点,但不代表说老百姓看得懂或者会跟它发生什么关系,所以这是特别需要时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当代艺术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实验、很先锋的艺术形态,如果能跟老百姓有有一些交集,那铺垫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一套艺术教育体系。
这当中有非常多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借鉴,就像比如说我今年在台湾的展览,美术馆虽然特别小,但他们做事情很专业,尤其在公共教育的职责上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比如说门票设计有很多种,包括针对普通观众、记者或是特殊票都不同,包括展览里设置了很多环节和公众产生联络,包括在我的展览期间不知做过多少遍导览、讲座,邀请其他的大学教授或艺评家去就展览所设计的话题也做讲座等,我觉得他们这种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感觉就是一个美术馆最应该做的,也是基本应该做的,只有哪天我们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能说我们的面貌会有所改变。
回到我们的城市和城市雕塑,谁都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城市雕塑,谁都知道很多东西就是垃圾,未来一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入垃圾堆的,根本不可能留下,这些城雕不代表我们的文化,也不代表当代,更不代表时代,但是这个东西花了很多钱,当时怎么会构成这样的状态?哪儿花这儿多钱买了一些这种无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这都是问题,可能做雕塑会常常被问到跟城市雕塑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在中国有非常复杂的渊源,非常复杂的生态,甚至说可能都构成跟艺术圈没什么关系的一个圈子,这常常是跟艺术本身是无关的,跟艺术判断是无关的,所以我觉得在任何城市如果你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雕塑也不用多想,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里必须要经过的。
雅昌艺术网:今年在台北的展览是您近些年来比较大的个展,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台北展览的情况?
向京:我觉得台北的展览是我这么多年来做的最大的一个个展,作品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大。参展作品包括《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主题下几乎全部作品,《全裸》的很多件作品,还有几件早期的作品串成一个可能的序列。一方面这样大型的展览需要作者像重新梳理自己一样去梳理,去考虑这些作品之间的联系,我自己以前总是强调我如何从身体这样的部分去离开和出离,走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样一种对于崇敬的表达里,本来我是强调这样一种分离关系。
但展览呈现出来之后,我反而看到的是它内在一种联系、一种线索,因为做作品的时候创作者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我状态里边,因为你面对的完全是一个问题,你考虑的是一个问题如何转换成一个视觉形象这样一种概念。所以你几乎是完全沉浸在这样一种转换和一种判断里面,你跟作品的关系非常紧密,连接几乎是不可分隔的一种关系,完全粘连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你常常会特别渴望看到它的一些可能性,一些意义,但是常常因为你关联太紧,看不到,看不清。我是觉得有一种概念文本的概念,当作品成为文本,这需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一个空间的。比如说现在我看全裸那个系列,我会讲得非常清楚,此刻我再去讲《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作品我也讲得清楚,但是在当时几乎是折磨我的,因为我又渴望通过看到这些意义鼓励自己能继续下去,认为自己这个东西是可以自圆其说了,另一方面又因为看不清完全是在这种煎熬里边倍受折磨。
现在我说我隔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现在时间又久了之后在台北的展览把相对完整的形态整合在一起,甚至于说我原来觉得我的作品是一块一块的,搁在一起之后发现当中有一个线索是内在有联系,因为展览是一个一个小房间,本来我认为这是不同系列,但搁在一起又构成一种新的语境,非常有意思,不同系列在一起仍然会诞生新的一个情景,非常有意思。这对创作来说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这也是像雕塑这样的立体作品能够达到的东西。这个确实给了我特别美妙的一个经验。
另外一点,碰到好的展览空间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台北这个展厅我喜欢极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台北就去过这个美术馆,第一次看到那个展厅时我想哪天在这儿做一个个展就好了,没有想到真正有一天梦想成真,而且这个空间跟我的作品有一种一致的质感;包括我所讲的心理情境,我一直很想在展览里边营造一个所谓心理情境,在这展览里边特别好地显现出来,因为有点儿像每个房间一个单独的空间,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从这个故事到另外一个故事,走到一个地方发现一个新东西,走了一圈之后你自己头脑中构成一个东西,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是特别完美,在我做展览所有的经验里边,这次是做得最细致的一个展览,包括很多细节。
据说这个展览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打破两个记录,一个是布展速度最快,因为我对这些作品太熟悉了,我几乎非常能准确地捕捉到应该诞生的一种情境。第二个记录是破了今年参观人数的记录,这个展览看的人最多,这个展览真的很美妙,给我整个的感觉非常美妙。